这问题,问得有点意思。
第一反应,脱口而出,不就是 苹果 嘛。一个两岁小孩指着水果篮子都会说的词。简单,直接,毫无悬念。
但你再琢磨一下,这事儿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如今当我们在中文语境里说出 “苹果” 这两个字的时候,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,到底是什么?
是一只红彤彤、圆滚滚,咬一口嘎嘣脆,汁水四溢的富士苹果?还是那个被咬了一口的、泛着微光的logo,以及它背后那个冰冷、光滑的玻璃和金属机身?
说实话,我赌后者。
这就是这个词在当代中文里最吊诡、也最迷人的地方。一个普普通通的水果名词,在短短二三十年间,被一家科技公司彻底“绑架”了,甚至可以说,被重新定义了。
苹果,这个词的重心,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偏移。
我想起小时候,姥姥从集市上买回来的苹果,用衣角擦得锃亮,递到我手里。那时的 苹果,是具象的,是有温度的,是带着泥土和阳光气息的。它的味道是酸甜,是清脆,是童年记忆里最朴素的满足感。那时候,我们说“吃苹果”,就是字面意思,仅此而已。
后来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一切都变了。
大概是从iPod那小小的白色耳机线开始蔓延,再到iPhone 4那颠覆性的设计横空出世。苹果,不再仅仅是水果。它变成了一个符号,一种身份,一个代表着设计、创新和某种“酷”的文化图腾。
从此,“我买了个新 苹果”,这句话的意思就彻底变了。没人会以为你只是去超市买了二斤水果。大家心领神会,你在谈论的是手机、电脑、手表,是那个叫 苹果公司 (Apple Inc.)的商业帝国。
这种鸠占鹊巢,在语言学上简直是个奇迹。
你看,其他品牌,比如“小米”,虽然也深入人心,但你听到“小米”,依然能清晰地联想到那碗热腾腾的小米粥。它俩能共存。但 苹果 不一样,它的品牌形象过于强势、过于具有侵略性,以至于在很多场景下,它几乎要将那个水果的本意挤出我们的第一联想。
这种感觉就像你走在一条熟悉的街道上,突然发现你从小吃到大的那家包子铺,一夜之间变成了全球连锁的高级定制西装店,招牌还是那两个字,但里里外外,灵魂都换了。
更有意思的是它的翻译策略本身。
Apple 公司,当初进入中文市场,完全可以选一个音译,比如“阿婆”、“爱普”,听起来洋气,也符合很多外企的取名逻辑。但它没有。它选择了最朴实无华、最直截了当的意译—— 苹果。
这步棋,现在回头看,简直是神来之笔。
因为它直接把logo那个视觉符号,和中文词语完美地绑定在了一起。你看到那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,就想到 “苹果” 这两个汉字,反之亦然。这种视觉和语义的强关联,形成了一种极其高效的传播记忆。简单,粗暴,但有效得可怕。
乔布斯 当年选择这个名字,据说有各种各样的原因,比如他曾在苹果园工作,喜欢披头士的苹果唱片公司,或者只是想让公司的名字在电话簿里排在雅达利(Atari)前面。无论初衷是什么,这个名字在中文世界里,意外地长成了一棵超乎想象的参天大树。
现在,我们甚至基于这个被“污染”了的词,发展出了一系列新的词汇。
比如 “苹果全家桶”。这词多有画面感?它说的不是一篮子水果,而是指一个人拥有了iPhone、iPad、MacBook、Apple Watch等一系列苹果产品,被牢牢锁定在它的生态系统里。这词的诞生,本身就证明了 苹果 作为科技品牌的意义,已经远远压倒了它作为水果的意义。
还有每年圣诞节前夕,在中国莫名其妙流行起来的 “平安果”。人们把包装精美的苹果当做礼物,取“苹果”的“苹”与“平安”的“平”谐音。这本来是基于水果本身生发出的本土文化现象,但你敢说,当人们在挑选那个最贵、最漂亮的蛇果作为平安果时,心里没有一丝一毫被 苹果 公司的品牌光环所影响吗?我觉得,多少是有的。那个logo,那个品牌,无形中给所有的苹果,都镀上了一层现代、高级的微光。
所以,回到最初的问题。
Apple的中文翻译是什么?
答案是 苹果。
但这个答案背后,是一整个时代的变迁,是消费主义的狂潮,是全球化的烙印,是一场商业对日常语言的温柔入侵。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词语对等翻译。它是一个文化现象的浓缩。
一个词,两种人生。
一种是自然的、有机的、属于土地的。
一种是科技的、冰冷的、属于硅谷的。
而我们,就生活在这两种意义的夹缝里。有时候在菜市场,对着一堆红富士发愣,会突然觉得“苹果”这个词有点陌生;有时候在深夜里,滑动着手机屏幕,那冰冷的触感又无比真实。
这,或许就是语言的魅力吧。它永远在流动,在变化,被我们的生活所塑造,又反过来定义我们的生活。
苹果,再也不是那个单纯的苹果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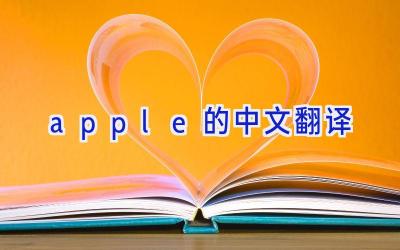
本内容由lily收集整理,不代表本站观点,如果侵犯您的权利,请联系删除(点这里联系)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jc.puchedu.cn/96527.html
